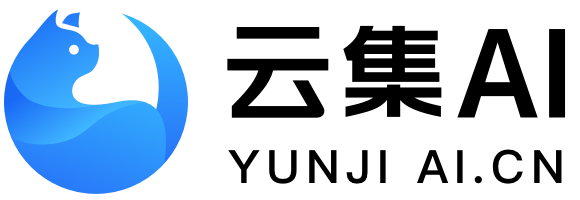30年软件老兵剖开AI真相:程序员价值失效、团队抗拒、裁员恐惧?管理者必答3问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一切。作为一名在软件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年的老兵,猫爷发现,衡量程序员价值的标尺正在失效,团队对新工具充满抗拒,而关于 AI 提效最终是否等于裁员的恐惧,正在团队中蔓延。面对这场巨变,猫爷认为,答案并不稀缺,重要的是问出正确的问题。这几天梳理一线的焦虑与困惑,他向自己,也向所有技术管理者,提出了三个问题……
猫爷入行的时候,Pony还在开发OICQ,丁磊还在给广州电信卖邮箱,大强子在中关村的买卖还没开张,马老师的中国黄页刚刚上线,雷布斯还只是天下第一程序员的小弟,每次想到这些,猫爷就老泪纵横,30年呀,干啥不好,非干开发这苦逼生意。
前几天看到卡帕西关于软件3.0的演讲,大意是大模型是未来的操作系统,自然语言是新的编程语言,而我们正处于软件3.0的命令行阶段,大家还不知道新的UI长什么样。
猫爷已经被技术浪潮洗礼了好几次,每一次都看到怀揣不靠谱梦想的小青年儿,变成了行业大佬,把自己活成了江湖传说,很多次羡慕嫉妒恨以后,猫爷体悟到,人性本质上是图省事儿的,给人省事儿的技术无论最初多么不靠谱,最后总是能成,而反人性的生意必须靠强大的力量推进。猫爷以为,生成式AI是继计算器和智能马桶以后,最让人省事的一个发明。
这次的浪潮有何不同
软件开发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鼓励偷懒、提高效率的演进史。从汇编到高级语言,再到后来的开发框架、开源社区和云计算,每一次改变都让开发变得更简单更高效。但这一次非常不一样,它不作用于工具链,而是直接改造了“思想”到“代码”的转化过程,大模型让代码本身变得空前的“廉价”。
这意味着,我们过去衡量程序员价值的标尺比如对框架的掌握、代码熟练度正在迅速失效。未来,工程师的核心价值将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设计优雅系统的能力,以及对AI生成物进行批判性审视的能力。“码农”必须进化成“建筑师”或“指挥家”。
这场变革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迅猛,去年大家还在争相囤N卡,今年老黄说华为的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春节全民都在讨论DeepSeek,现在Cursor已经被骂成了狗,大家都改玩Claude Code了,谁知道下个月会发生什么。
上个月奥特曼说,温和奇点可能已经到来,温和不温和猫爷可不知道,猫爷只知道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脑袋上就是一口锅,不想为AI背锅,就必须以跳跃性的思维,重新审视现在和未来,尽快找到正确的姿势投入AI的怀抱。
猫爷三问
猫爷的小公司是苦逼里的战斗机,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实在不能看着兄弟们一起饿死,一狠心,上了AI的梁山泊,下决心的时候,猫爷问了三个自以为很有深度的问题。猫爷以为,大模型时代,答案并不稀缺,重要的是问出正确的问题。
问题一 如何衡量人工智能的真实回报(ROI)?
从KPI到OKR,对软件工程师的绩效评估一直是猫爷手心里的一根刺。自打发现ChatGPT写代码特别好用,猫爷觉得自己又行了,单枪匹马写了一个人效管理工具,工程师们每天的“代码行数”、 “Bug修复数”查的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就会用不要钱的通义灵码了,每天提交的代码量蹭蹭的涨,但是项目该延期还是要延期,月底算账发工资的时候,猫爷还是心痛的喘不过气。
猫爷不服,又写了个代码分析器,tree-sitter分析代码库,自动调用SonarQube和DeepSeek,每次PR都给你们扫一遍,过程不是很愉快,而且扫出的问题工程师们有一大堆理由等着你。
真正的提效是后来猫爷自家的vibe coding平台上了线,开发效率肉眼可见的提高,手上的刺也不那么别扭了,现在猫爷最关注的是如何获得和评估AI带来的二阶效应:
• 创新的复利:当工程师从重复性工作中被解放出来,如何让他们将额外的精力,投入到那些为公司构建长期“护城河”的问题上?这种价值该如何评估,如何激励?
• 质量的飞跃:AI驱动的智能测试与验证,可能会让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性大幅提升,这对于用户信任和品牌资产的提升,意味着什么?在AI协同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持续的质量改进和用户体验增强?
• 人才结构的变化:一个初中级工程师在AI工具的加持下,成长为一专多能的人才,这种能力的提升与资深工程师的经验价值如何平衡?企业和管理者如何适应这种人才结构的转变,AI可能为企业带来怎样的长期回报?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猫爷认为衡量AI的ROI,需要一套更宏观、更着眼于长期的价值框架,只计算节省了多少成本,格局就小了,真正要关心的是创造了多少新的可能性。
问题二 如何理解和应对团队对新工具的抗拒?
猫爷公司内部刚刚开始推广AI编程助手的时候,团队的AI采用率极其的低,而且资深工程师们对所有编程助手全部不屑一顾,代码质量问题,幻觉问题,上下文窗口问题等等说了一大堆,猫爷认为这些道理都毫无道理,盘算着组织培训上奖惩机制,直到有一个做AI智能体的同行说他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接任何以减员增效为目标的AI项目,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们过去一年做了150多个POC,成功率大约5%,这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猫爷恍然大悟。
当引入新工具却收效甚微时,我们常常归因于工具本身或培训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往往根植于人性的基本规律和激励机制的错位,码农们虽然寡言木纳,但智商在线,你老小子引入AI工具,嘴上说着提效的好,心里却憋着减员的坏,还让老子自己给自己挖坑。
查理·芒格说:“如果你想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猫爷以为,团队的抗拒,通常源于几个非常朴素的担忧:对自身价值被取代的恐惧;对“黑箱”工具不可控性的疑虑;以及改变既有工作习惯所带来的认知负荷。
有效的做法,不是强行推广,而是改变激励机制,使之与我们期望的行为保持一致,
• 重新定义价值:明确地告诉团队,他们的价值不再是“写代码”,而是“解决问题”。AI是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杠杆,是放大他们智慧的工具,而非竞争者。
• 建立信任:从小处着手,选择那些能立刻看到显著成效的场景,让团队亲身体验到AI带来的“甜头”。当他们发现新工具能让他们更早下班、工作更有趣时,接受度自然会提高。
• 投资于“新技能”:未来的核心技能,是如何与AI高效协同。我们应该大力投资于新能力的培养,比如提问工程和这几天新提出的上下文工程,并让那些率先掌握这些技能的成员,成为团队新的榜样和老师。
问题三 AI提效是否必然导向“裁员”?
这是一个关于“增长”与“分配”的经典战略选择题。
如果一个组织选择不拥抱生产力的提升,那么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它会因为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逐渐失去阵地。到了那个时候,裁员将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无奈的结局。所以,拒绝进步的代价,远比拥抱进步的阵痛要大得多。
而对于那些成功利用AI提升了效率的组织,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是把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红利”,简单地用于削减成本、裁撤人员?还是将其再投资于新的增长曲线?全世界都在经历经济下行的痛苦,这时选择前者是最安全的做法,但最大的赢家一定是来自后者,因为巨大的效率提升,意味着他们可以用同样的团队,去探索过去因为资源限制而不敢尝试的新领域;意味着我们可以让最有经验的工程师,去攻克那些最核心、最复杂的挑战问题。
猫爷以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企业的格局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价值创造中心”,AI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杠杆。
最后的思考:警惕“幸存者”的傲慢
猫爷以为,AI对软件行业的重塑是不可逆转的,这既是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然而70后,80后,甚至90后的老板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不是AI本身,而是我们作为“幸存者”的惯性思维。当老的组织还在为内部流程、ROI计算、以及员工的适应性苦恼的时侯,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往往来自于那些没有历史包袱的边缘地带。
最早出生的00后已经25岁,他们从小玩着抖音和iPad,有着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直接的思维方式,这些被AI武装到牙齿的超级个体和超级小组们,没有冗长的会议和复杂的汇报关系。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百分之百地拥抱新的生产范式,而且战斗的主场是他们从小就熟悉的舞台。他们能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效率,创造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并直接挑战现有巨头的根基。这或许才是这场变革中,最值得老炮儿们警醒的一幕。
猫爷以为,面对未来,重要的不是给出所有答案,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带领我们的组织,保持谦逊、保持开放,勇敢地踏入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也充满无限可能的新时代。